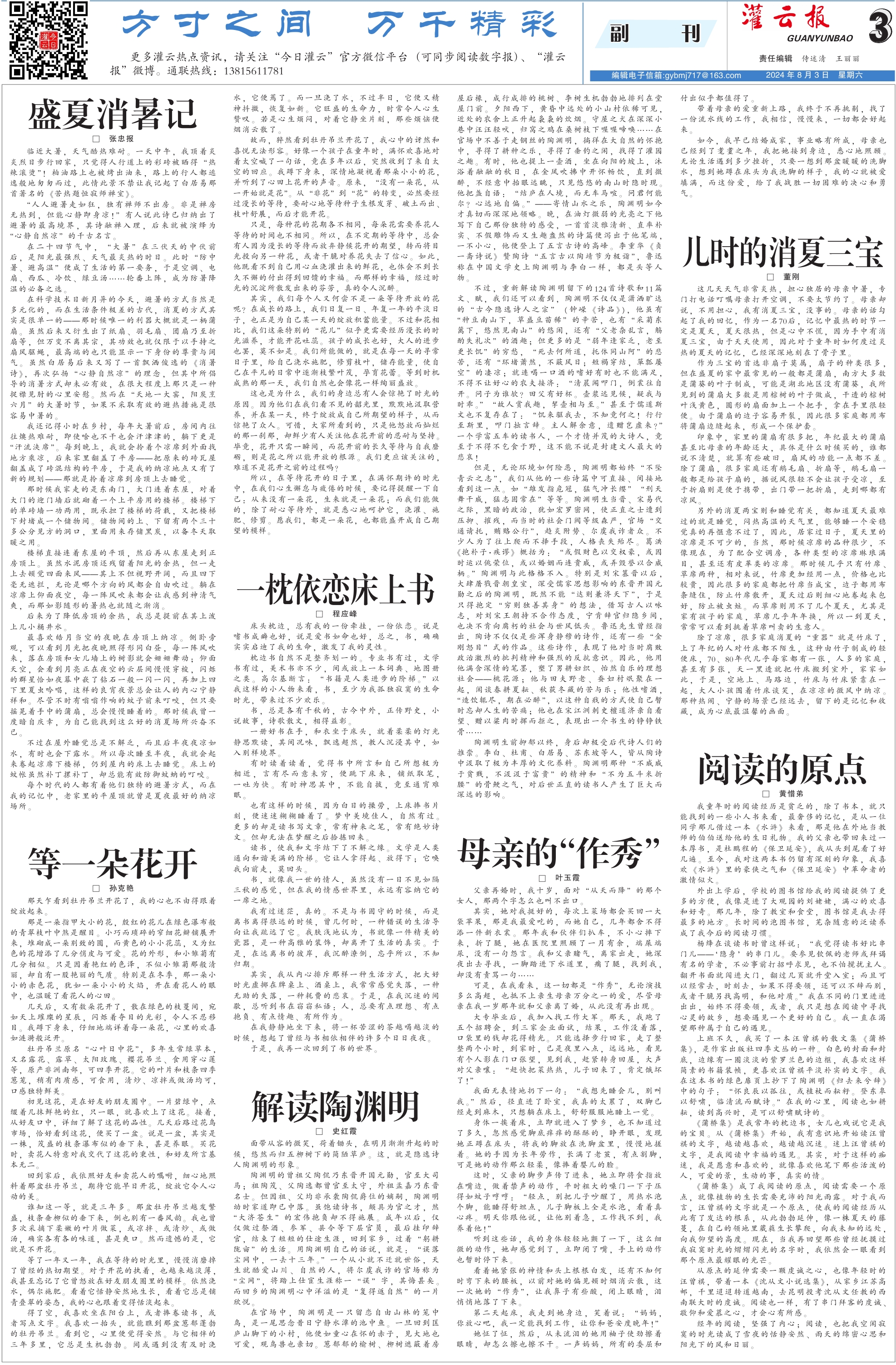□ 黄惜弟
我童年时的阅读经历是贫乏的,除了书本,就只能找到的一些小人书来看,最奢侈的记忆,是从一位同学那儿借过一本《水浒》来看,那是他在外地当教师的伯伯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我的父亲也带回来过一本厚书,是杜鹏程的《保卫延安》,我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。至今,我对这两本书仍留有深刻的印象,我喜欢《水浒》里的豪侠之气和《保卫延安》中革命者的激情似火。
外出上学后,学校的图书馆给我的阅读提供了更多的方便,我像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,满心的欢喜和好奇。那几年,除了教室和食堂,图书馆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。长时间的泡图书馆,芜杂随意的泛读养成了我今后的阅读习惯。
杨绛在谈读书时曾这样说:“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——‘隐身’的串门儿。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,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,也不怕搅扰主人。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,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;而且可以经常去,时刻去,如果不得要领,还可以不辞而别,或者干脆另找高明,和他对质。”我在不同的门里进进出出,始终不得要领,或者,我只是想在阅读中寻找心灵的故乡,想要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我一直在渴望那种属于自己的遇见。
上班不久,我买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《蒲桥集》,是作家出版社四季文丛的一种。白色的封面和封底,边缘有一圈淡淡的紫罗兰色的边框,我喜欢这样简素的书籍装帧,更喜欢汪曾祺平淡朴实的文字。我在这本书的绿色扉页上抄下了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句子:“怀良辰以孤往,或植杖而耘籽。登东皋以舒啸,临清流而赋诗。”在我的心里,阅读也如耕耘,读到高兴时,是可以舒啸赋诗的。
《蒲桥集》是我常年的枕边书,女儿也戏说它是我的宝贝。从《蒲桥集》开始,我有意识地开始读汪曾祺的文字,越读越喜欢,越读越沉迷。迷上汪曾祺的文字,是我阅读中幸福的遇见。其实,对于这样的痴迷,我是愿意和喜欢的,就像喜欢他笔下那些活泼的人,可爱的景,生动的事,真实的情。
《蒲桥集》成了我阅读的原点,阅读需要一个原点,就像植物的生长需要充沛的阳光雨露。对于我而言,汪曾祺的文字就是一个原点,使我的阅读经历从此有了发达的根系,从此勃勃延伸,像一株夏天的藤蔓,在自己的领地里葳蕤生长攀爬,向我未知的远处,向我仰望的高度。现在,当我再回望那些曾经抚摸过我寂寞时光的熠熠闪光的名字时,我依然会一眼看到那个原点最耀眼的光芒。
从原点的延伸需要一颗虔诚之心,也像年轻时的汪曾祺,带着一本《沈从文小说选集》,从家乡江苏高邮,千里迢迢转道越南,去昆明投考沈从文任教的西南联大时的虔诚。阅读也一样,有了串门拜客的虔诚、敬仰和爱慕之心,才会心有所感。
经年的阅读,坚强了内心;阅读,也把我空闲寂寞的时光读成了雪夜的恬静安然、雨天的绵密心思和阳光下的风和日丽。